马振骋先生的法语翻译工作是从退休后才开始的。他最初的翻译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几个代表作:《夜航》《空军飞行员》《人的大地》和《小王子》,它们都收入了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空军飞行员》一书中。当小王子要离开自己的星球去旅行时,他和玫瑰花的对白,在马先生的《小王子》的译文里,是这样的两句:
“分别啦,”他对花说。
但是花没有回答。
“分别啦,”他又说了一遍。
其他译者基本都把这句翻译成“再见了”,更有甚者翻译成“别了”。每次和马先生见面后,我都想说声“分别啦”。只有在马先生的译本里,我才能感受到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的出尘,他并不用生僻的语词,却说着和所有在地面营营的人类都不一样的话,小王子的语言。

音乐性
我第一次见马先生,他就告诉我,在四篇译作里,他最喜欢《人的大地》。初读它,我只以“抒情散文”来看待它,觉得它写的是飞行员生涯的壮烈、慷慨,是动人的战友情谊,是个人探索天宇的远大抱负。后来复读,感受才逐次加深,每每有新发现;它的文字里有一种梦幻感,有和成年人口吻迥然不同的骄傲的孩子气。
马先生告诉我,这个作品的开头,他起初照着字面翻译成这样:
“大地比全部书本更多地教给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因为它抗拒我们。人在跟障碍较劲时发现了自我。”
顺吗?不顺。他跳了过去,过了很久,他才回到头上,把该句改译成了这样:
“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来自大地,更多于来自书本。因为土地桀骜不驯。人在跟障碍较量时,才会发现自己的价值。”
音乐性。在马先生长乐路的老房子里,进门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被墙角里潺潺流出的音乐所环绕。修改后的句子轻重顿挫,在“桀骜不驯”和“自己的价值”之间形成了一种节奏感。音乐推动着人,慢慢松开初见原文时的拘谨,而产出的译文又迥异于以中文为母语的人能写出那类“美文”。

马先生1980年代以来的早期译作里,有一本塞斯勃隆的《被扼杀的是莫扎特》,书名很特别,出版时间是在书业审美寒酸的1992年。当我问起此书,马先生解释了一下,原来也与《人的大地》有关。在《人的大地》的尾声,作者讲到自己坐火车,一整节车皮,装的都是经济危机期间被遣散回家的波兰工人,他们衣冠凌乱,面孔粗糙,此起彼落地打着呼噜,被列车无情地送回黯淡的命运中去。这时,一对熟睡的夫妇之间,一个孩子引起了作者的注意,他干净的脸上大张着两眼,好奇地东看西看。
在《小王子》里,圣埃克苏佩里同样写到,大人在车厢里不是睡觉就是哈欠,“只有孩子把鼻子贴在玻璃上张望。”而在波兰工人的车厢见到那孩子,他则感叹,“这是一张音乐家的脸,这是童年的莫扎特”,但这个莫扎特,恐怕会早早被扼杀的,一如他疲于奔命的父母那样,脸上心中,再无儿时的神采。
马先生告诉我,他译到此处是何等地受触动。于是在《人的大地》完工时,马先生又找来了一本法国小说,书名就叫《被扼杀的是莫扎特》。塞尔日·塞斯勃隆是一位有良知的法国小说家,他写了此书,写一个被不良的家庭早早遗弃到社会上,从而浪费了天赋的孩子的悲剧。它呼应了《人的大地》里的严峻发问:怎样让更多的孩子不要长成俗物,而是经智慧的吹拂成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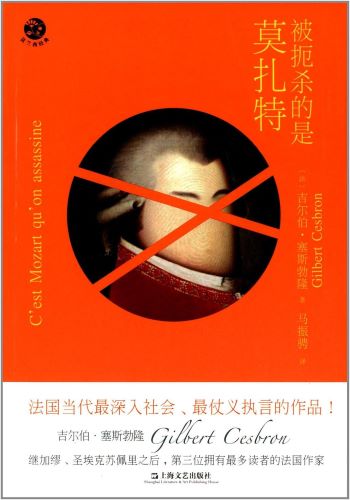
“此刻”之人
我认识马先生时,他的翻译刚开始呈现多产的态势。海南出版社那时出版了他选译的《要塞》,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的笔记,原作的总量很大。先生讲起他的选译理由:“圣埃克苏佩里也是在飞行的间隙写的,写得太多,很多是重复的,有的意思不大”。出版社在正文前放了一篇周国平写的长文,把马先生的“译序”排在了第二。我有心发点非议,先生却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弄”。
他一向如此言语,不是没态度,而是不爱讲废话。圣埃克苏佩里(1900~1945)紧张的一生里更容不得废话,笔记里的重复是因为他在不同的时刻谈论类似的主题,无暇核实与精编。读《要塞》,就像读《蒙田随笔》一样,二十来岁的人是很难真正看进去的,我能做的只是提笔摘抄,摘抄的是《要塞》里的第二节,相比漫长的第一节,第二节的句子忽然有所明朗:
“平安来自满满登登的谷仓、沉睡的母羊、折叠整齐的衣服,平安来自完美,平安来自做成以后立即献给上帝的礼物。”
依然是节奏感在起关键作用。但一个驾驶飞机的人怎么还会念念不忘上帝?他难道不该目空一切吗?这是我当时的疑问,实际上,紧挨着的下一段就有解答:
“因为我觉得人跟要塞很相像。人打破围墙要自由自在,他也只剩下了一堆暴露在星光下的断垣残壁。这时开始无处存身的忧患。他应该把嫩芽萌生的清香、母羊剪毛时的气息看作是他的真理。……要塞,我要把你建造在人的心坎里。”
马先生译的《要塞》就此把一幅月光下的废弃要塞的场景建在了我的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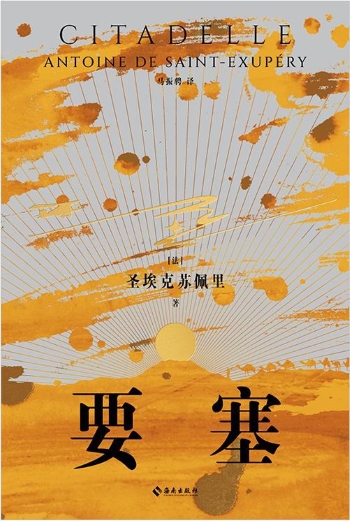
在我眼里,先生是个“此刻”之人,唯一重要的都是此刻的事,手头的事:刚翻译了什么,刚注意到什么,要着手进行什么。他从未说起师承,从未讲早年如何“爱上文学翻译”等等;我也从未想到要去打问。和《要塞》几乎同期,他译的《艺术心灵驿站》也出版了,这本书讲19世纪的精神病大夫埃米尔·白朗希在巴黎开办疯人院和文艺沙龙的故事,可说是“掌故”一类,而马先生说起来,就仿佛说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件路人皆知的日用品:
“白朗希大夫的疯人院里关过很多有名的法国文化艺术界的人,莫泊桑啊,夏尔·古诺啊……”
夏尔·古诺是谁,我就不知道。过了几年,他又翻译了《自由派作家们》,又是法国文人的掌故;又翻译了《克里姆林宫故事》,这回是和法国有关的俄国的掌故。先生翻译的书实在是太多,在如杜拉斯、纪德、昆德拉、圣埃克苏佩里等名作家的书之外,还有无数文艺掌故、知识小品,单是多达近百本的法国小丛书“发现之旅”系列,他就译了其中五六本,主题从纽约,到耶稣身世,到阿兹特克文明,到文字与书写的历史,形形色色。
他必然知道不是什么书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不管是《小王子》《要塞》这样的名作,还是《克里姆林宫故事》这种很普通的掌故小辑,无一例外地都具有他眼里的“趣味性”,翻译本身就是增长见识,如此而已,正是翻译《人的大地》,激发了他翻译《被扼杀的是莫扎特》的兴趣,也正是翻译《克里姆林宫故事》时对俄国积累起的了解,让他在数年后又翻译出了一本讲东欧解体后的俄国故事的《搅局者》。见马先生其人,很难产生“渊博”的印象,唯觉他的“此刻”总有话说。像是《克里姆林宫故事》刚出的时候,他一如以往,仿佛是在说一种他早就知道、也料想我早就知道的常识:“法国和俄国的关系,那是太密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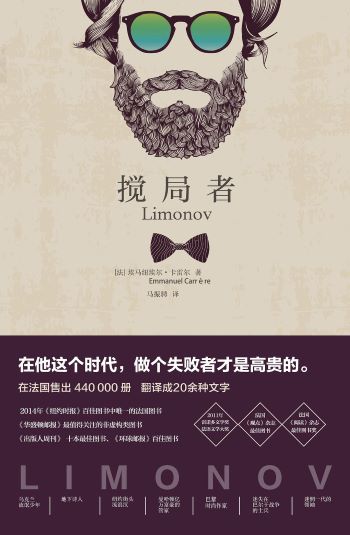
翻译许多书的人,在闲聊中难免爱指点人一二:某某书在法国可是大名鼎鼎哦!某某书随便看看,没什么大意思——诸如此类。但马先生很特别,他讲书中的内容,讲作者的思想,却不给书分档次。他用同样的语气讲《人的大地》和《艺术心灵驿站》,用同样的“此刻”感谈昆德拉与蒙田,只要一谈起,就是现在时。2011年,《蒙田意大利之旅》即将出版前夕,我去拜访马先生,他说:
“蒙田去过意大利,写完随笔之后他就去了。他有一个秘书,这个秘书讲蒙田的事情讲得非常详细,特别讲到蒙田治病的情况……”
他翻译的这本书,但讲起它的时候,他更像一个刚刚读过书的读者,想要把书中最有八卦味的东西说给人听。确实,蒙田的八卦也是八卦,在一个秘书的笔下,蒙田不是作家和大贤人,而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病人:先是肾移位,服用山扁豆泻药、威尼斯松脂和味道类似杏仁奶的三种饮料;一个月后,又是恶性腹绞痛,“排出许多沙子,后来又是一次大结石,硬而光滑,在尿道停留了五六个钟点。”这位秘书,每写到蒙田的病症及治疗时,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一颗一颗地清点主人拉出来的结石,甚至闻闻吃完药后排出的尿。——我后来自读这本《蒙田意大利之旅》,忽然想,马先生能如此平视他的译作,不也是因为他是这么一位时刻在场,紧跟作品和文字,并计点其中细节的“秘书”吗?
遇到和分别
2011年时,马先生已称得上“译作等身”,并得到了重量级的肯定:他译的《蒙田随笔全集》获得了第一届傅雷翻译奖——和张祖建译的罗兰·巴尔特《埃菲尔铁塔》平分。但《埃菲尔铁塔》一书其实是巴尔特的单篇文章,蒙田随笔全集可是三大卷;我遂爱说一句玩笑话:本来抽颗闲烟就能得奖,马先生却偏要中大烟瘾。

我的意思是,翻译蒙田,打磨蒙田译文,成了先生一生的事业,也是他保持成长的基本方法;在《随笔》之后,《蒙田意大利之旅》《马背上的蒙田》等,都是他意犹未尽下译出“蒙田周边”。他和蒙田一样,都爱猫,喂猫,任目光追随着猫,而且蒙田是双鱼座,2月28日生人,于是,我料想3月出生的马先生,和法国人蒙田实有一种趣味上的相通和相投。
按照星座性格的讲法,2月28日的人,兴趣太广,热心而活泼,“最好是能够坐下来。好好地想一想自己要做啥,行事要谨慎点。”——完全切中蒙田,在《随笔》里,他跟着自己的个性任意东西,这里探一探,那里拱一拱,正是因为好奇心太强,他的身体和头脑在每一条道路上都闯荡过,从而知道在每条路的尽头,人都会变得要么(身体)痛苦,要么(头脑)疯狂。
马先生书房里无奇不有的译作,还有自己写的几个法国文化随笔集,很难说不是“好奇心太强”的后果。但他和蒙田更显明的共同点,是谦抑。蒙田非线性的写作里,箴言遍地盛开,但这些句子,都不是供人拿来训诫他人的,而是让人默记于心、安静领会的:
“自高自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病,所有创造物中最不幸,最虚弱,也是最自负的是人。”
“世上很少事情,我们能够给予一个诚心诚意的判断,因为世上很少事情我们不多多少少掺有个人利益。”
“我们使用这些字眼时神气十足,如杀、偷、背叛;而关于生殖行为,却只敢在牙缝里嗫嗫嚅嚅地说。这是不是说我们愈是不用言辞表达的东西,愈是有权利在思想里夸大吗?”
蒙田的随笔,让人朝“人”回归,而非反过来,把自己擢升到“人”之外和之上。那么,在蒙田随笔里摸爬品嚼了那么多年,马先生当然最清楚,这首先是蒙田写给自己读的文章,是他给自己的所思所感赋予的可读形态,唯其谦和自抑,这思想和感受才得以流传;故而,它们甚至是不可能被拿来“传授”的,它们只能被“遇到”,人在二十岁时很难,在三十岁、四十岁,遇到的几率就大大增加。它们可谓智慧,智慧是路过的风,路过月光下的要塞,路过有待吹拂的泥胎。
我自己做翻译的时候,也曾向马先生请益。他常常很严厉,不乐意解释一些他认为我应该知道的东西,挂电话时咔的一声很响。《三国演义》里对东吴丞相顾雍有四个字的评语:“严厉正大”——他是这样的人,尽管我懂得他的谦抑,尽管我懂得,他不适合求教,更适合遇到,更适合遇到他的人说声:“分别啦,谢谢你。”
帮企客致力于为您提供最新最全的财经资讯,想了解更多行业动态,欢迎关注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