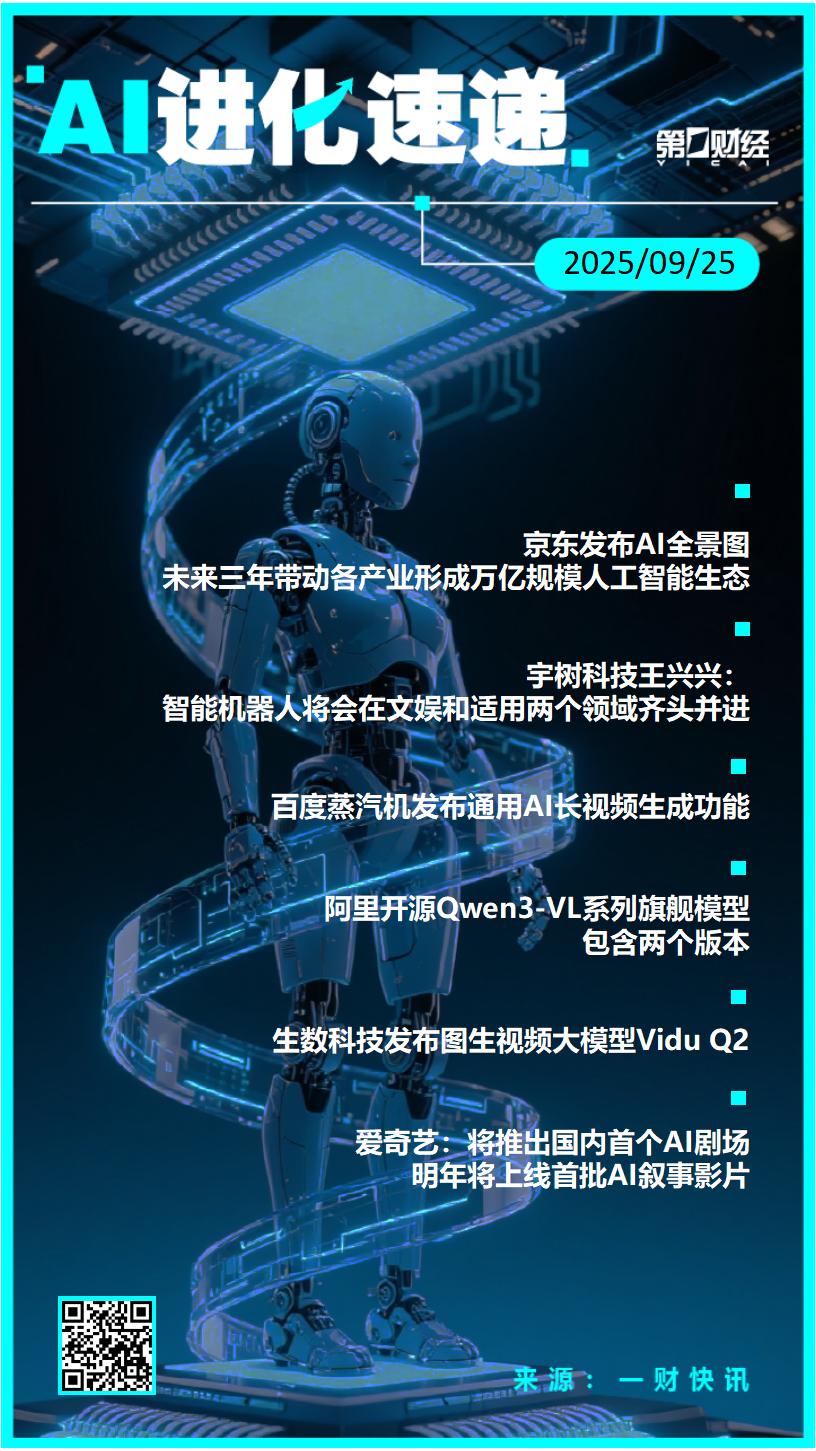2025年9月24日,山东日照附近海域,伴随着火光和轰鸣,火箭升空,12颗卫星成功入轨,吉利星座一期迎来组网收官。至此,时空道宇共有64颗卫星在轨运行,这意味着中国商业航天已经具备全球实时物联通信覆盖的能力。对CEO王洋来说,这一刻并不只是一次成功的发射,而像是行业走到福特T型车下线的那一刻:卫星终于不再只是国家的专属项目,而是通过星座服务正在走向普通人。

纵观技术史,每一次伟大变革都遵循着类似的轨迹: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但真正让汽车进入千家万户的,是亨利·福特制造的T型车和汽车流水线;莱特兄弟让人类第一次飞上天空,而真正让航空旅行成为人们日常的,则是波音707的规模化生产;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但让互联网从学术界走入千家万户的,是AOL的拨号上网。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相机最初是笨重昂贵的实验设备,柯达推出便携式相机和胶卷业务后,才让大众摄影时代成为可能……发明家点燃火种,企业家才让火种照亮所有人。
在当下,卫星,也在经历这样的转折。
2018年成立的时空道宇,如今已成为全球少数能独立建设和运营低轨星座的科技公司,也是国内首家通过整轨部署完成星座一期组网的商业航天企业。在这背后,是一个关于“卫星技术平权”的故事——王洋,一个80后工程师,如何在十二年间,把曾经需要举国之力才能完成的技术,一步步变成未来参与我们生活的万物互联基座。
一个工程师的抉择——从0到1,走出商业航天创新之路
早在上个世纪,王洋的父亲就是北大荒农场的一名拖拉机手,与机械朝夕相伴。父亲对机械的熟练程度,到了闭着眼都能把整车拆卸再组装的地步。或许正是这种骨子里的工程师气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王洋。少年时代的耳濡目染,让他对机械与技术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后来,他在大学时就选择主修计算机系的软件工程,把这种亲近感转化为一种系统性的技术训练。
2004年,中国的互联网正处在狂飙突进的时刻。百度刚刚崛起,阿里巴巴拿到当时国内最大的私募融资,盛大网络在纳斯达克风光上市。很多年轻人把互联网视作黄金赛道,而王洋却选择了进入华为。
这并不是一条看上去“顺风顺水”的道路。当时的华为正经历外部冲击与内部改革,但也正是在那里,王洋见证了通信行业从2G跨入3G的关键节点。他亲眼看到,先进技术如果不能服务于用户,最终不过是一堆冰冷的设备。而一旦技术和市场结合,就能迅速改变数以亿计人的生活。从那时起,他在心底埋下了一个信念:技术的意义,不是证明自己能做到,而是让更多人用得起。

后来,王洋进入中科院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从最基础的星务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做起,开始了真正的“航天人”生涯。他几乎干遍了所有岗位:从卫星软件工程师,到型号项目经理,再到国有航天企业的总经理。每天都在与编程打交道的三年,他一步步熟悉了从卫星整星、地面测试系统到AIT环节的完整链条。经手的所有项目无一失败,他从工程师一路成长为项目经理、再到国企管理者,成为一名体系内炙手可热的“全能手”。
这段经历,是王洋最自豪的资本之一。它们让他具备了对航天系统工程的客观认知,日后在管理民营企业建设低轨星座时,才有能力应对复杂度极高的工程挑战。可与此同时,他也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一些现实局限:“我们能把卫星送上天,却很难让卫星真正服务大众。”王洋说。
摩托罗拉的“铱星计划”是一个警醒。1990年代,摩托罗拉斥资50多亿美元,组建了66颗卫星的全球通信网络,技术领先于时代,却因为成本过高、应用不足,仅仅存活了16个月就宣告破产。它证明了卫星通信的可行性,却也让世界看清:如果没有普惠性的商业模式,再伟大的技术也会坠落。
王洋在2014年做出了他的抉择。他判断,随着元器件价格下降,低轨卫星通信的“福特时刻”正在逼近。随着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发展商业航天,他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浪潮之中,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航天公司欧科微航天。此后,2018年他出任上海格思信息执行董事、兼任母公司中科辰新总经理,这期间,他推进了两项从0到1的开创性工作:一是建立卫星量产能力,二是打造契合商业卫星需求的上游供应链体系。这些探索,为后来的时空道宇的成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航天基因融合造车基因——实现卫星量产AIT创新
也是在2018年,王洋遇见了李书福。一个是从中科院出走,连续创业的航天工程师;一个是以“造车狂人”著称,正把触角伸向新能源、芯片和航空航天的知名企业家。两人很快找到了共识:地球只是起点,未来属于太空。
就这样,时空道宇成立了。它不是简单的创业公司,而是一家罕见地把航天基因、汽车制造基因和通信基因融合在一起的企业——王洋担任CEO兼首席系统工程专家,李书福则提供战略支持。

团队初创时堪称“豪华配置”:18位创始成员中有14人是工程师,平均航天经验15年,参与过40余个国家重大型号,包括北斗二期/三期、遥感三十号、风云系列。CTO是北斗三号载荷负责人,总工程师曾是遥感型号的核心设计师,许多人都曾担任卫星型号的总指挥或副总师。毫不夸张地说,这相当于两支完整的“国家队”走出来创业。
王洋深知,航天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个人英雄主义绝不可能成功。他在公司推行“双轨制”:一方面保留航天的工程严谨,确保每一个环节符合标准;另一方面引入互联网的敏捷开发,让年轻工程师也能一年就能跑完一个卫星项目周期。这种速度在过去行业内是不可想象的——快速迭代,不断试错,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卫星规模化落地的速度。在这里,资深的总师与初出茅庐的“00后”并肩工作,跨界的碰撞常常发生。卫星设计师会和汽车工程师一起讨论如何把天线嵌入车玻璃,通信专家也会和物流工程师一起优化物联网终端的功耗。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2021年。台州的卫星超级工厂正式落成,王洋把汽车制造的脉动式流水线逻辑搬进了航天制造。过去,卫星往往是“孤品”,每一颗都要定制,如同手工艺品。现在,它们被拆解成两百多个标准模块,像搭积木一样可以快速组合。测试环节也高度自动化,从设计到下线,卫星的周期被压缩到28天,成本下降了一个数量级。
这意味着什么?就像福特的流水线让汽车从“贵族玩具”变成了“工人也可以买得起的代步工具”,王洋要用工业化逻辑让卫星也能走出实验室,开始一个规模化生产的时代。在工业化的逻辑里,卫星不只是“造一颗”,而是可以“日产一颗”。

在这个过程中,吉利的造车基因给予了灵感。汽车工业是全球规模化制造的典范,讲究标准化、可复制、成本控制和质量追溯。时空道宇借助吉利的制造体系,把这一套经验移植到航天制造上,从而把卫星变成可以支撑商业闭环的产品。
另一关键突破是供应链整合。早在2014年,王洋就带队开始全栈自研“嘉定一号”的平台电子学单机,并在遥感三十号星座完成国内首次量产测传单机批量交付及北斗星上RDSS载荷交付。在设计阶段,将昂贵的宇航级元器件大批量替换为车规级元器件,这一创新尝试足以颠覆传统航天产业链。十年几百台自研单机在轨运行,证明了这种“低成本 高可靠 可批量”的模式可行。可以说,正是工业化和供应链改革,让卫星第一次真正走上了量产之路。
卫星组网提供规模化商业服务,走向全球万物互联
对王洋来说,卫星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能上天”,而是要“能落地”。过去几十年,地球上的通信网络一直追求更快、更宽,但仍有70%的区域缺乏地面信号——无论是荒漠、海洋,还是高山、极地,信号常常消失在地图的边缘。正是在这些空白处,卫星物联网络将成为信号的真正基座。智能汽车、无人机、物流车队、货轮渔船和能源设施的数字化需求,也会越来越依赖“无处不在”的连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吉利星座选择了一条与星链不同的路径。星链的重点是面向个人宽带,而时空道宇的重点,是从产业切入,把卫星物联通信变成万物互联的底座。时空道宇曾提出过吉利星座有三期规划。一期的规划就是用72颗(64颗 8颗备份卫星)实现全球实时通信覆盖。设想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围绕一个现实问题展开——如何能先找到能支付得起也必须用得上的场景,才能考虑逐步走向大众。

汽车是最佳突破口。2023年,极氪001 FR率先量产配备时空道宇自研车载卫星通信技术,让车主即便身处无地网区域也能发消息、打电话。时空道宇与曹操出行达成战略合作,为自动驾驶车队提供卫星通信与高精定位服务。对普通用户而言,这意味着即使家人在无人区自驾,依旧能无障碍随时报平安。对城市管理者而言,这意味着上千辆车队在复杂路网中依旧能精确运行。这些场景的实现依赖的就是卫星,让网络保持实时在线。
汽车之外,卫星还在深入更多产业——工程机械可以在偏远工地实时上传数据,渔船可以在深海区域持续回传作业情况,电力和石油设施可以在荒漠戈壁得到远程监测,应急救援队伍可以在灾区保持通信。每一个场景背后,都是地面网络难以触达的空白。卫星填补了这些空白,让“万物互联”变得完整。
王洋特别强调“开源开放生态”,时常会把时空道宇定位为一家科技平台公司。“我们的模式像早期的Linux或Android,全栈自研之后,全栈开源。” 王洋说。在他的构想里,卫星是全球战略性基础设施,应用则是长在其上的生态。
这种战略选择,也让时空道宇在国际竞争中形成差异化。星链、OneWeb卷的是互联网,而吉利星座卷的是物联网——一条更贴近中国和新兴市场需求的路径。中东、非洲、东南亚、中亚、拉美……这些地方的“弱地网带”正是卫星,特别是卫星物联网最有价值的战场。2024年至2025年,时空道宇已经与二十多个国家的运营商达成合作,把“星座—地面站—终端—应用”的链条一点点打通。王洋也坚持自主可控的原则,时空道宇自研了星载计算机、导航增强载荷、星间链路等关键部件,累计数百项专利。如今,公司已实现从设计、制造、测控到运营的全链路自主化,通信成功率高达100%。

自此,时空道宇已经完成了一个清晰的商业闭环——在生产端,卫星超级工厂让制造成本大幅降低;在发射端,公司采用“整轨部署”的战略,大幅提升组网效率;在应用端,则在星座建设的同时就着手推动落地场景。截止到一期组网完成时,时空道宇已形成了覆盖商业航天产业的全链条拓展。可以说,这一整套打法,代表了当下中国商业航天的先进生产力。
回看技术史,正如AOL的拨号上网曾经把互联网从实验室带进千家万户,吉利星座正在把卫星从发射场带入汽车、海洋、农田、港口与工厂。也许用户并不会意识到自己在使用卫星,就像人们不会去数城市里的5G基站。但当求救短信在无人区被顺利送出,当自动驾驶在山谷中依旧能有精准定位信息,当跨洋货轮实时回传航迹时,卫星已经静悄悄地成为生活的一种“日常”。
“我们要做的,不是让卫星看起来多么伟大,而是让它像空气和电力一样自然存在。”王洋说。对他而言,卫星不是孤立的器件,而是未来万物互联的路网。现在,它已经开始服务全球。而未来,它将像基站一样,支撑起我们万物互联的数字生活。也就是说,卫星创新的故事,这还只是开始,真正的大规模商业化图景才刚刚向我们展开。
帮企客致力于为您提供最新最全的财经资讯,想了解更多行业动态,欢迎关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