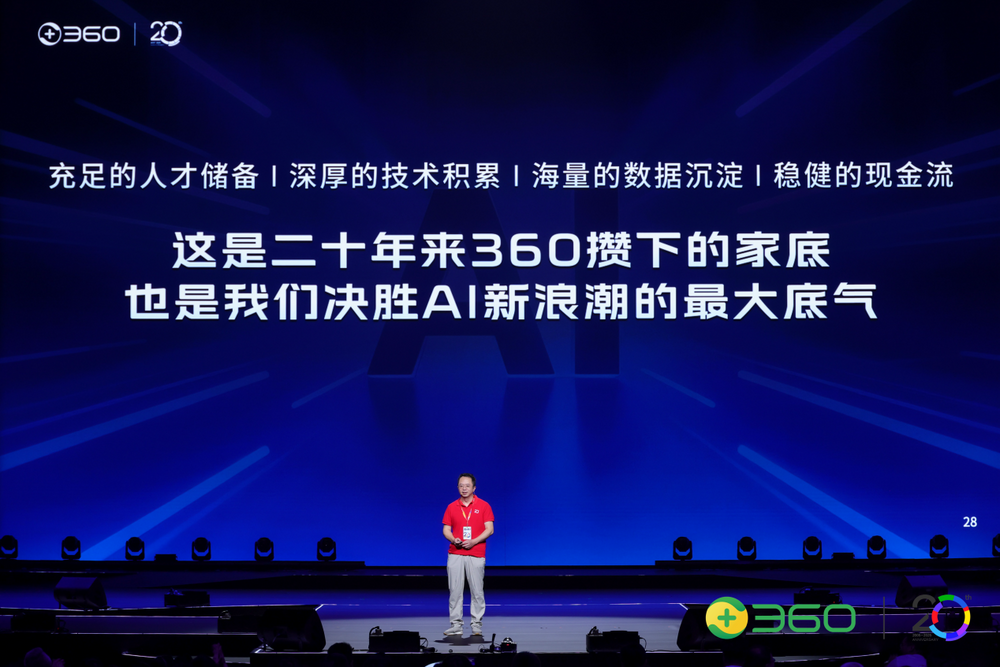1961~1975年的越南战争对世界影响深远,其伤痛对美越双方来说都延续至今。不过过去的越战史研究,一般聚焦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及其带来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文化运动。最新出版的《墓地中的军营:越南的军事化景观》则是一本独辟蹊径的“军事环境史”著作,研究越战对越南本土环境持续至今的影响。作者大卫·比格斯是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与一位越南裔美国学者结婚使他成为越南的“洋女婿”,一定程度上也帮助他有了审视越战的全新视角。
在中文世界里,近年环境史方面的好书层出不穷。第一财经曾推荐过《什么是环境史?》《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等,《流动的森林:一部清代市场经济史》曾获评第一财经2024春季书单历史类好书。这三本书都属于光启书局“人与环境”丛书,《墓地中的军营》则是该丛书最新推出的作品。
丛书编辑肖峰认为,以往的历史讲述习惯于以人为中心,环境史则着重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墓地中的军营》的英文原名可直译为“战争的足迹”,有一种隐喻性:“把战争对一片土地留下的印记比作人踩出的脚印。后来人走过这个地方,往往都会踩到前人走过的路,后来发生的战争,它的空间往往都是继承了过去战争留下的空间。”
带着这种“足迹”思维,比格斯在书中聚焦以承天顺化省为中心的越南中部地区,向前追溯到从15世纪开始的早期战争、19世纪开始的法国殖民入侵、二战时期日本的入侵,到二战后越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美国的入侵。他在书中回顾了军事活动反复在沿海低地和山区高地展开的逻辑,深入剖析反复发生的军事冲突如何构建了当地的景观、生活和记忆。
反思“创造性破坏”
1972~1973年,美国从越南的撤军过程揭示了这场战争给越南带来的诸多伤痕,既有环境的,也有社会层面的。被毁坏的基地和被炸毁的山丘是可见的伤痕,不可见的则包括当地家庭生活和文化风俗的断裂。比格斯在观察中发现,美军喜欢将越南人的乡村墓地改造建设军营,这就是中文书名《墓地中的军营》的来源。

起初,美国工兵在建造基地时,将当地越南人的坟墓推平,引发了当地的骚动。此后,他们只能在坟墓周围建造基地。贯穿越南南北的1号公路是运输的大动脉,但很多地方周边可用空间有限,美海军陆战队开始在村庄中的墓地扎营,这给很多美军士兵和越南百姓都带来影响。去扫墓的越南人可能被士兵开枪击中,美军老兵的回忆则往往伴随着这些墓地的记忆,一些人说混凝土墓地墙体经常帮助他们躲避火箭弹和狙击火力。
1973年,比格斯的父亲作为一名曾在核动力航母上工作的核工程师复员回家。在那之前,比格斯多年跟随父亲生活在军事基地,是一名典型的成长于越战阴影里的美国小孩。他在大学里成为一名环保活动活跃分子,随后开始研究越南。2006年,在顺化富牌国际机场附近调研时,比格斯看到一片由村庄和新工厂组成的密集地带,有几十片杂乱的空地,路面破损,没有房子。越南导游告诉他,这里此前都是美军营地,导游本人也是南越老兵之子,在这些基地附近长大。

像这类受战争影响产生的空地,也许在地产大开发当中,有机会变成新的建筑物和街区。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军事行动清除了地表原本的事物,产生了一种“创造性破坏”,空荡荡的足迹为新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军事行动、军事占领或许成为打开新市场和开启资本密集型机会的一种手段。但在二战末期的原子弹爆炸后,以奥本海默的反思为起点,人们开始认识到“创造性破坏”这一说法存在的问题。这种逻辑可能不再成立,留给战争土地的可能是长久的化学污染和核辐射,还有更多东西是现有科学技术无法清理或需投入巨大成本才能清理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贾珺是《墓地中的军营》的译者,他早在2005年就在中文世界引入并丰富了“军事环境史”这一概念。2023年,贾珺出版了《慎思与深耕:外国军事环境史研究》一书,回顾了环境因素与人类军事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双向互动过程体现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自然观变化。贾珺认为,比格斯的这本书在表面现象之外,对越战之后的“创造性破坏”提出了更深入的思考。
比格斯把战争废墟在冲突结束后持续存在多年视为一种“破坏不彻底”的结果。贾珺进一步指出,二战核爆之前,战略空袭造成的主要是物理破坏,比如柏林、德累斯顿、考文垂等城市,大部分建筑物被炸毁,那么推倒重来的改造复建是可能的。而从越战开始,持续的大规模化学性破坏造成了极大影响。美国军方主动使用化学品摧毁当地环境,加剧越共军队在补给与藏行动踪迹等方面的困难。“牧场工”等喷洒落叶剂的行动,并未考虑对人的健康及环境长久的影响,所用化学物质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对当地生态和人员身心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透过军事理解人的能动性
贾珺提到,比格斯在书中记述战争中弱势一方如何应对,也形成了十分经典的军事环境史叙事。化学战除了带来国际政治和本地政治的争议,也带来了新的生态挑战,比如对阔叶植物实施的落叶计划。在有针对性地清除阔叶植物后,橙剂又创造了新的草原。越共军队很快适应了这种情况,开辟了新的道路,增加了新的伪装。老兵们适应了凝固汽油弹的攻击,先是把适应青草的浅绿色伪装改为适应落叶树木的灰色伪装,当凝固汽油弹轰炸山坡后,再把伪装变成黑色的,他们会用烧黑的木炭覆盖自己的身体。
“这些对越共士兵如何应对美军行动的记载,生动体现了人作为主观能动性很强的智能生物,在不断变化的军事环境中,努力保存自己、继续战斗。”贾珺表示,这个例子也说明,军事环境史与军事地理学是非常不同的,后者的立足点是天然的地理环境因素,并不涉及战争开始之后,战争双方在具体地理环境条件下的攻守作战,及其带来的变化与相关应对。
2007年,比格斯在一次活动中,向承天顺化省科技厅厅长说明了自己对战争遗留问题的关注。对方恰好负责该省有毒废弃物的清理工作,问他是否可以通过美军旧基地的记录帮助确认废弃物的地点。当时,有当地工人发现美军废弃的生锈铁桶后,被里面的化学物质伤害。这些废弃物还引起越南有关方面彼此之间的财务和法律纠纷。
比格斯的建议后来得到批准,得以应用其环境史研究展开一个大规模的项目。《驻东南亚美军档案》是世界史上有关军事占领最详细的公共档案之一,文字记录多达几百个书架。比格斯在其中发现了相关美军基地化学活动的详细记录,包括使用橙剂等战术除草剂和批量投掷桶装CS(催泪瓦斯的常见成分)粉末的行动。他还运用美国的航空照片和地图,对美军基地“鹰营”和“富牌”的历史图像与地图进行了数字化比对,借助遥感技术,将历史图层和最新的卫星图像作比较分析,在长期历史地图上标记出了化工场所周围的裸露表面。

贾珺认为,军事环境史研究的应用前景,更多是从历史遗产保护和未来宜居性的合理化分析方面提出建议,而非直接对军事污染地点去提出治理建议。“军事环境史不一定从破坏和反破坏的角度体现价值,而是发挥历史学人和历史学本身的价值。”他提到,现在发生的巴以冲突、俄乌冲突中的被破坏地区,主要是物理性破坏,而非越战中的化学性破坏,比格斯参与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少见的。
比格斯自己也更看重这些协助土壤修复的工作所牵引出的历史,他对富牌机场的历史追溯,可以延伸到15世纪初越南和占族军队与明朝军队发生的战斗。17世纪末以来,这里就是冶铁废料倾倒区,持续到1800年的铁矿开采留下了大堆废渣和植被退化的山丘,而这恰恰满足了1924年法国殖民政府找空地修建机场的需求。在之后的50年里,日军、越盟军队、法国陆军、南越军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越南人民军先后接管该地,不断变更其周边的用途和部署。直到2000年以后,这里仍有一些军事用地,但“富牌工业园区”已经拔地而起。新的基础设施和大批打工的妇女成为这里最日常化的景观。
正如贾珺所言,人类的军事活动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军事环境史要探讨的内容。《墓地中的军营》中写到的越南人如何尽己所能地利用曾蒙受战争冲击的家园土地,既令人感慨,也颇具启发性。

《墓地中的军营:越南的军事化景观》
[美]大卫·比格斯 著
光启书局 2025年1月版
帮企客致力于为您提供最新最全的财经资讯,想了解更多行业动态,欢迎关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