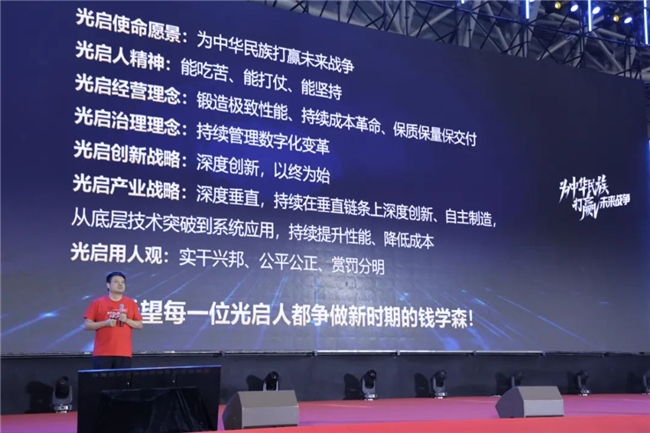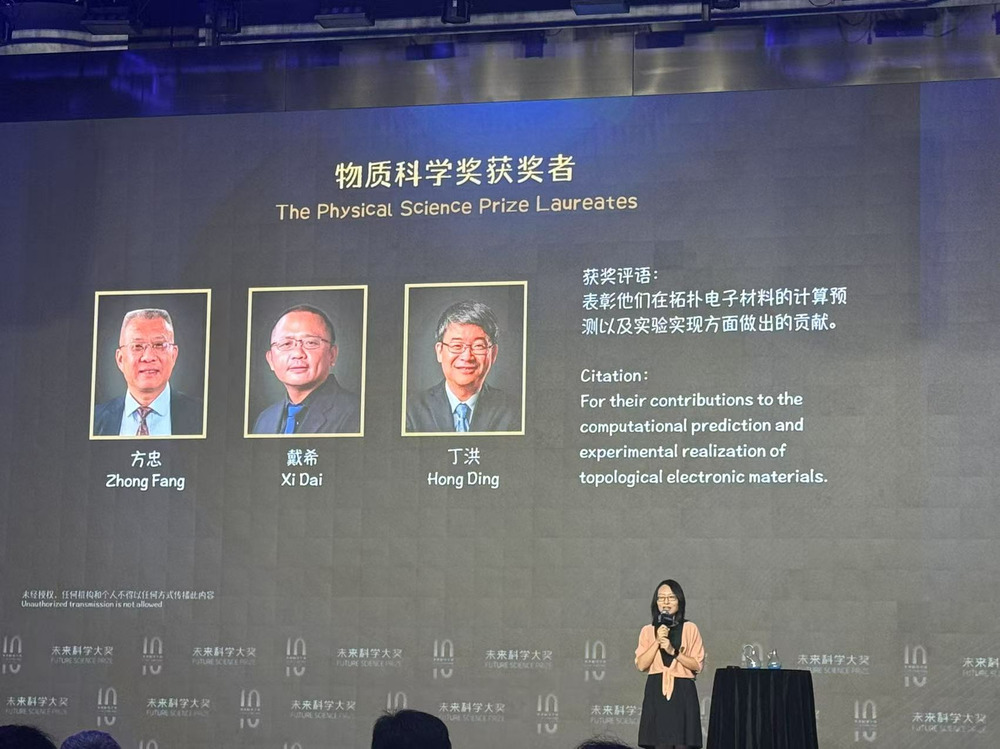【编者按】住进大埔永盛坪山巅的庭院,才懂得邻居二字,未必指人。推开门,是山。关上窗,云就来了。大埔的山,性子是慢的。它不急着向你展示什么,只...


住进大埔永盛坪山巅的庭院,才懂得“邻居”二字,未必指人。
推开门,是山。关上窗,云就来了。

大埔的山,性子是慢的。它不急着向你展示什么,只在你晨起推窗的刹那,把一整夜的酝酿——那片无垠的、流动的云海——平铺直叙地推到你的眼底。没有预告,没有喧嚣,像一块巨大的、微凉的丝绒,轻柔地覆盖着沉睡的谷壑。空气是湿漉漉的,带着草木根茎深处渗出的清冽,深深吸一口,肺腑便如同被山泉洗过一遍。

所谓“日出”,在这里并非壮烈的喷薄,更像是一种温柔的渗透。天色先是晕开一层极淡的灰蓝,接着,云海的边缘开始泛出微光,不是刺目的金黄,而是带着水汽的、近乎透明的暖橘色。光仿佛有生命,在蓬松的云絮里小心翼翼地流动、晕染,缓慢地溶解着夜的墨色。山峦的轮廓在光与云的游戏中时隐时现,像几笔淡墨洇在宣纸上。没有声响,只有风拂过竹林梢头细微的沙沙声,和不知名早鸟偶尔一两声短促的清啼,更衬得这天地间的静默。

日子,便在这云卷云舒、光隐光现中流淌。

雨后,云海开始升腾、变幻,成了悬在半空的大片纱幔,将远山裁剪成朦胧的剪影。捧一杯本地的山茶,看热气袅袅上升,竟分不清是茶烟融入了云气,还是云气落入了杯中。茶味清苦回甘,喉间一片沁凉,思绪也如那云一般,松散开来,无所依凭。手中翻着的书页,常常停驻许久,目光却飘向了窗外那片永恒的流动。时间在这里失了刻度,只以云的形态为标记。

在泊心云舍·山里客家住久了,那翻腾的云海,那每日如期而至又绝不雷同的日出,便成了生活最恒常的背景。它们不再是需要刻意“观赏”的奇景,而是像呼吸的空气、饮下的山泉,自然融入每一个晨昏。

心,竟也像被这山间的云雾淘洗过,滤去了许多芜杂。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看最后一缕霞光敛入云层深处,山影四合,虫声渐起。炉灶上煨着简单的山野时蔬,热气氤氲。那一刻的安宁与满足,无需言说,只在胸腔里微微鼓胀,如同山间悄然弥漫的薄雾。